马上注册,三台事早知道!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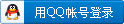 |
|
x
它,诞生自春秋战国,有着皇室贡品的高贵血统
它,独属于中国美食,又专注于巴蜀风味
它,承载着时代风雨的烙印,是家乡味蕾上的乡愁
它,多次斩获国际国内的美食大奖,是舌尖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
它,叫潼川豆豉,是美食大咖必备的调味佳品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潼川豆豉的前世,与幽菽有关的过往
关于它的前世,得从它的名字说起。
往去十万年,人类繁衍生息的足迹,从山川密林,刀耕火种中学会了创造劳动工具和生产种植的本领,将野生杂草培育成了五谷杂粮,并从此诞生了人类得以战胜自然、赖以生存的伟大产业——农业。
上溯几千年里,因农而兴、因农而盛的国家和朝代,比比皆是。祭天地,重农事,从神农氏尝百草,到封建帝王事躬农耕。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,老祖宗们的谆谆教导,让生存的意义,从文化的根基里注入了人类进步的基因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千百年来,我国农耕文化厚重,自有“五谷丰登”的说法。早在先秦时期,一代大贤孟子就曾有“树艺五谷,五谷熟而民人育”的赞誉,是故风雨时节,五谷丰登,社稷安宁。据《周礼》记载,“五谷,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”。其中菽,指大豆。
“民之所食,大抵豆饭藿羹”,在汉代以前,大豆是人们重要的粮食。赡养父母,养育子女,甚至行兵打仗,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。关于豆豉的发明者,早已淹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埃中,那时候它不叫豆豉,而是被极其赋予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古人,取名为幽菽,并衍生出了一个独属于好吃嘴的形声字“嗜”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与豆豉有关的创造发明,据《百度百科》记载,“豆豉约创制于春秋、战国之际。屈原的名篇《楚辞.招魂》中有‘大苦咸酸’,根据注释大苦即为豆豉。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先秦文献无豆豉,当是秦汉之际出现。《史记.货殖列传》始见豆豉记述。”汉代刘熙所著的《释名.释饮食》一书中,誉豆豉为“五味调和,需之而成”。宋代周密著《齐东野语·配盐幽菽》也有这样一段文字讲述与幽菽有关的故事:“昔传江西一士,求见杨诚斋,颇以该洽自负。越数日,诚斋简之云:‘闻公自江西来,配盐幽菽欲求少许。’士人茫然莫晓,亟往谢曰:‘某读书不多,实不知为何物?’ 诚斋徐检《礼部韵略》‘豉’字示之,注云:‘配盐幽菽也。’然其义亦未可深晓。” 明代杨慎著 《丹铅杂录·解字之妙》:“盖豉本豆也,以盐配之,幽闭於瓮盎中所成,故曰幽菽。”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《周礼》曰: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。”《孟子·告子》曰:“食色,性也。”“人莫不饮食也,鲜能知味也”,作为享誉世界的美食大国,在与人类美食有关的过往中,从来不缺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。与推动世界人类科技革命的十大发明创造相比,从杜康创造出酒,到西周之前发现醋,再到先秦时期创造出豆豉,中国人对美食的创造和发现,在世界美食文化之中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。
到公元2至5世纪,崔浩所著的《食经》,从生产研发上系统提出了“作豉法”,为豆豉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到南北朝时期,我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《齐民要术》,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、食品的加工与贮藏、野生植物的利用,以及治荒的方法,详细介绍了季节、气候、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,被誉为“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”。书中也明确记载了豆豉的技法。
潼川豆豉的兴盛,与三台有关的渊源
据史书记载,豆豉作为调味品最早兴于江西泰和县,古称庐陵,位于素有“江南一等富庶地”之称的吉泰平原,此处河网纵横,自古为江南望郡、商贸重镇。到了公元1670年,也就是清康熙九年,在湖广填四川的时代大迁移中,一个姓邱的家族,惯于做豆豉,他们揣着这份手艺,跟着人口迁徙洪流,来到了潼川府,也就是今天的三台县。在享誉东川的涪江水运码头上,舟来船往,商贾繁忙,他们在水运码头的南门外安下基业,做起了水豆豉的买卖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潼川府,地处四川盆地川西北丘区,位于长江上游重要支流涪江的中段,恰恰处于北纬30度这条神奇维度的附近,山川秀美,景色宜人,气候温润。初入巴蜀,巴山夜雨涨秋池的独特气候,与江水如平沙的涪江,让邱氏家族萌生了改进生产技术的想法,结合潼川府的气候和水质特点,他们创造出了独特的“毛霉制曲、常温发酵”的生产工艺,这便有了色鲜味美的潼川豆豉。六年后,也就是公元1676年,清康熙十五年,清军收复福建,讨伐云南王吴三桂的当年,时任潼川知府进京向孝庄太皇太后祝寿,也就是给大玉儿过生日,将潼川豆豉作为礼物,进献给她。大玉儿品尝后,赞不绝口,遂下旨将潼川豆豉定为宫廷御用珍品。从此,潼川豆豉就成了四川每年进献的皇室贡品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一时之间,潼川豆豉声名远扬,并逐渐发展成川菜的必备调味品之一,有了“潼川豆豉保宁醋,荣隆二昌出夏布”的美誉。邱氏家族的子孙邱正顺创办的“正顺号”酱园,年产20多万斤,收益巨丰,人称“邱百万”,开启了潼川豆豉规模化生产的历史。到了清道光11年,也就是公元1831年,邱氏家族的潼川豆豉兴盛了155年,潼川城内的商人卢富顺和冯朴斋两家从邱家聘用技术工人,在东街和老西街先后开办了“德裕丰”、“长发红”酱园,与邱家展开了竞争,由此,潼川豆豉从一家独大逐步发展成多家竞争经营的特色产业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出门三五里,忽闻异香飘。
借问是何物?豆豉一大包。
类似此种童谣,在民间声声不息。据《三台县志》记载:“城中已大资本开设酱园者数10家,每年造豆豉极为殷盛,挑贩络绎不绝。”
从一家之货,到皇室贡品,再到相互竞争,潼川豆豉远销全国,走入了寻常百姓家,成了居家必备的调味珍品。
在经历了封建王朝覆灭,民国动荡,全民抗战,再到新中国诞生,更名为三台县的潼川,作为抗战的大后方,全力发展生产,让潼川豆豉在战火硝烟中,逐步壮大发展起来。
到1950年,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,潼川豆豉的生产厂家已经达到45家,开启了潼川豆豉最为兴盛的时代。

1956年初,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,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。三台城内26家个体酱园成立公私合营三台城关酿造总店,以三个车间生产潼川豆豉。至此,个体酱园的兴衰更替画上句号,而潼川豆豉则走上了规范化、规模化、企业化的发展之路,迎来了新的发展春天。1982年,潼川豆豉评为省优质产品,并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,先后荣获中国食品博览会、全国食品大赛、巴蜀食品节金奖。
经过36年的发展,到1992年,潼川豆豉的产量已达3000多吨,成了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。
潼川豆豉的今生,与时代有关的蝶变
一个时代,有一个时代的发展过往;一座城,有一座城的兴衰更迭;一个品牌,也有一个品牌的生存逻辑。
进入上世纪90年代,在经历极致发展的巅峰之后,在不进则退的时代大潮中,已有316年历史的老字号潼川豆豉,由于经营不善,市场竞争力弱,逐步从巅峰滑向了低谷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1992年,这是潼川豆豉的命运转折点。
在经历了11年的生死挣扎后,2003年,入不敷出的潼川豆豉公司无法维持,于当年8月宣布破产重组。
人们常说,有舍才有得。置之死地而后生,破茧成蝶的秘密和勇气,来自于潼川豆豉根植于美食文化中的响亮口碑。正是凭着作为川菜的独一味道,破产重组后,成立了四川省三台县潼川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作为潼川豆豉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杨静,在父母的影响下,对潼川豆豉有着常人难以割舍的情缘,她懂得这份味道的可贵,更明白它所面临的艰难。她毅然出资成立了公司,接过了潼川豆豉这块金子招牌,如何让它重新发光发亮,怎样让它蝶变新生。杨静拜师马永开、李宾儒两位传承人,专注技艺传承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三年的光阴,三年的味道,用了三年的时间,杨静将这份手艺传承了下来,并迅速打开市场,重获一席之地。到2006年,潼川豆豉的产量已经达到六七百吨,产值2000万左右。潼川豆豉酿制技艺,作为目前我国唯一采用手工毛霉制曲生产豆豉的传统工艺流程,先后被县政府、市政府和省政府,公布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;2008年6月7日,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2014年,潼川豆豉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杨静将潼川豆豉的生产车间从县城搬到了芦溪工业集中区,建起了新厂房和潼川豆豉博物馆,并与西南科技大学食品酿造系合作,引进现代酿造技术,结合传统酿造工艺,对潼川豆豉生产流程进行了重要调整和创新。目前,公司拥有潼川牌豆豉、长发红牌调味料等调味品数十个,产品畅销全国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从重生到蝶变,是一个艰难的过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虽然与巅峰时期相比,潼川豆豉要走的路还很长,但经久岁月的沉淀,老手艺,新思路,它的味道反倒是越陈越香......
潼川豆豉的味道,与乡愁有关的情韵
食在中国,味在四川,舌尖上的美味从来都寄予了魂牵梦绕的乡愁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从哪里来到哪里去,人生A4纸上的空格,不过是近千个月,三万多天。而乡愁的味道,从来都是超越了单个的人生,单个的家族,跨过了一代又一代,过去了千年又千年,时间越久,历史越长,传续越深,自然是越陈越香,越久越浓。
从王侯将相,到普通百姓,《周礼》早在先秦之前,就已经表明了人对于饮食的重视,并因此形成了传续已久的礼制。“饮食男女”一词,即使放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依然那么新潮、那么时尚、那么精准。孟子说得更加透彻:“食色,性也”。
从形声字“嗜”的诞生,到今天满大街的“好吃嘴”,食色性也,人们对美食味道的追寻,可谓是开天辟地,又永续创新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潼川豆豉的味道,是中国人民对世界饮食文化的伟大发明和伟大创造。在物质匮乏的汉唐之前,大豆的种植和推广,绝不亚于稻子的意义。在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之余,人们通过对生产生活的总结,创造出了幽菽,并将其作为美食的调剂品和治疗疾病的药物,这是对大豆这种物种的再创造和再发明。正是通过这种发明创造,相继发明了酒、发现了醋,创造出豆瓣、豆腐,丰富了人生五味,开启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永续创新,并不断地植根在我们世代相传的血脉之中,成为滋养我们品格和肌体的重要基因。这种越陈越香,越酿越浓的味道,是我们独立于世界的乡愁。
爱上一种味道,正如爱上一座城的眷恋。潼川豆豉的味道,就是这般魂牵梦绕。它从春秋战国的血脉中传承下来,在“湖广填四川”的民族大融合中,创新发展,它所推进和衍化的每一步技艺,都烙印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对美食的追求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潼川,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城,自古就有“川北重镇、剑南名都”的美誉。这座蜀中巨屏,饱经风雨变幻,而又不断融合发展。在它的传续之中,我们何其有幸生在这里,长在这里,我们又有何其有幸传承了这份技艺,并创造出了潼川豆豉这个属于四川、属于中国的品牌。往溯三千年来,潼川府标注着四川的发展轨迹,而又回溯到三百年里,潼川豆豉则影响着川菜居于中国五大菜系之一的历史地位。
回锅肉、麻婆豆腐、川味豆豉鱼等等这些家喻户晓、人人爱吃的居家川菜之中,如果少了潼川豆豉的调味,川菜就不再是名副其实的的川菜,它就像掉了魂,失去了它独立于世界美食之林的四川味道。潼川豆豉呈黑褐色,颗颗油润发亮,散发着厚醇的酱香,食之圆润化渣、滋味绵长、齿颊留香,从视角和口感上拉升了川菜的魅力。如果说郫县豆瓣是川菜的鲜,中坝酱油是川菜的色,阆中保宁醋是川菜的香,那么潼川豆豉则是川菜的魂。有了潼川豆豉这种愈久弥新、融合有度的魂,享誉全球的川菜让饮食男女的味蕾愈加鲜香舒畅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我们父亲的那一辈,他们比我们幸运。他们曾经见识过潼川豆豉的辉煌时刻。潼川豆豉的生产工厂,从县城遍布各镇乡,甚至于一些出产大豆的乡村,也都有酿造豆豉的人家。收大豆、卖大豆井然有序。那时候,工业技术并不发达,除了县城的工厂在不断用新技术进行改进,农村的绝大多数作坊和人家都还是肩挑背扛,脚踩手挖,用一个大砧子将煮熟的大豆压实发酵,熬过整个冬天,生出白色的霉菌,等到来年装进坛子,腌制两三年,方才掏出了装袋装盘子,摆在街头上叫卖。漆黑发亮,如同一颗颗新掏出来的黑珍珠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甚为遗憾的事,我们这一代人无缘见证潼川豆豉过去的风光。但每每走到南门大街,那种从岁月中飘荡出来的乡韵乡愁,还是让人忍不住地想起它的味道。老城墙里,一口千年龙眼水井,一坛坛褐色的土罐,一簸箕一簸箕晾晒发酵的大豆,掀开一层白纱布,满眼长着白发的霉须,滴着晶莹的水珠,还未装坛子,那扑面而来的醇香,就止不住地让人流口水.....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走一步,回望一眼,忍不住加快一阵子脚步,飞快地窜进自家的厨房。打燃灶台,洗漱锅碗,切上半斤五花肉,撕下五六个辣椒,切上生姜葱蒜,烧热铁锅,煎好肉片,再切开一袋潼川豆豉,抓上一把撒入锅中和着肉,一阵使劲翻炒爆香。炒出一大盘子的回锅肉,倒上一杯烧酒,美美地吃上一回。
“出门三五里,忽闻异香飘”,300年前的童谣仿若眼前,蝶变新生的潼川豆豉,依然还是那么香、那么浓,那么让人痨肠寡肚.....

离家越远,年岁越大,对潼川豆豉的想念,就越发浓厚。甚至于,外出打工或者是到外地出差,要住上一段时日,背囊里都要仍不住揣上几袋。没有它的调味,仿佛就吃不下异乡的美食。骨子里,就像我们喜好辣椒一般,舍不得,放不下,离不了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相信不久,潼川豆豉将走出国门,走向世界,让更多热爱美食的人爱上它的味道,爱上它的品格,爱上它独有的乡愁。
来源丨玩遍三台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