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上注册,三台事早知道!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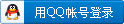 |
|
x
被誉为“诗圣”的杜甫于唐朝乾元二年冬为避“安史之乱”,辗转来到成都,开启了“五载客蜀郡,一年居梓州”的生涯。
唐宝应元年秋为避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的叛乱,再次流寓梓州(今三台县)近两年。而杜甫之所以选择到梓州,除了因为这个被誉为剑南名都的蜀中第二大都市对他的深深吸引外,还因为其好友严武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。

杜甫诗风现实,为人也比较沉稳,不像李白那样任性。可是有一次他竟然对他的恩人、四川最高军政长官严武发起飙来,跳到床上指着他的鼻子大骂:“没想到严挺之竟然有你这种儿子!”,导至严武欲杀掉杜甫……(注:严挺之,严武的父亲严浚,字挺之,唐朝著名大臣。)

关于此事的具体情节,多部史书都有记载:《旧唐书.杜甫传》云:“(甫)尝凭醉登武之床,瞪视武曰:严挺之乃有此儿”。《新唐书.严武传》云:“武以世旧待甫甚善,亲入其家。甫见之,或时不巾,而性褊躁傲诞,尝醉登武床,瞪视曰:严挺之(武父名)乃有此儿!武亦暴猛,外若不为忤,中衔之。一日,欲捕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,集吏于门。武将出,冠钩于帘三,左右白其母,奔救得止,独杀彝”。
严武欲杀杜甫时,犹豫再三,时而把帽挂上,时而又取,绯徊不定,下属看出严武心思,忙告知其母,严母立即过来劝阻……要不是严母,恐怕杜甫真的会因此而送命。
据说李白的《蜀道难》就是听说此事后,担心杜甫的安危所写。
杜甫酒喝高了,骂严武的话很重,换任何人都要发怒。这其中有几个因素。一则,杜甫父辈和严武的父辈都是官宦名臣,而且是世交,杜甫虽然比严武大7岁,但他们从小就以官二代而称兄道弟;现在杜甫直呼其父名,而且骂他是不肖之子,当然有辱其高贵血统。二则,杜甫和严武很有交情,二人在朝廷做官时就有交集,后来严武做了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,杜甫流落到成都,严武对杜甫多有关照。他不但请杜甫当幕僚,还向朝廷举荐,让杜甫得了个工部员外郎的官衔,享受副部级待遇。三则,杜甫写过很多赞美严武的诗。既然如此,杜甫陡然翻脸不认人,大骂严武,这似乎也太不知天高地厚,甚至有点忘恩负义,情商不高?作为堂堂名相之后、现在又官居要职、手握一方生杀大权的严武,当然就非常气恼,由此而起了杀心。

那么,杜甫为什么要对严武发飙呢?难道杜甫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吗?不是。是个不知好歹、绝情寡义的人吗?不是。是个狂妄冲动,不知利害,不顾后果的人吗?不是。是精神出了问题,一时发疯了吗?当然更不是。杜甫是正常的、是清醒的、他之所以这样做,完全是因为严武的问题。
其实,严武原本就是个毁誉参半的官员,此人抵御外患有功,曾击败吐蕃军七万多人,但他猛悍有余,仁义不施,而且生性暴戾。严武年青时自持是名相之后(官二代),他“优游京师,颇自矜大,初为剑南节度使,旧相房琯出为管内刺史,琯于武有荐导之恩,武骄倨,见琯略无朝礼,甚为时议所贬”。严武在镇守四川时兼任剑南节度,权利极大,更是专横跋扈。有史料记载:“严武前后在蜀累年,肆志逞欲,恣行猛政。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,及是小不副意,赴成都杖杀之,威震一方。蜀土颇饶珍产,武穷极奢靡,赏赐无度,或由一言赏至百万。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。而性本狂荡,视事多率胸臆”。《新唐书.严武传》也明确评价严武“穷极奢靡,赏赐无度”。
杜甫做了严武的幕僚之后,对严武的为人日渐了解,对他的残暴恶劣越来越反感。开始,杜甫还想加以规劝,曾经作《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》一诗和《说旱》一文进行讽谕和谏诤,但都没能让严武有所触动。杜甫感到很失望,只好在诗中多次托病辞归,反复要求离开严武幕府。这样一来,严武对杜甫就冷淡了,两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。因此,杜甫是在极为反感、义愤的情况下才对严武“酒后吐真言”发飙的。
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南宋末至元初著名书法家、画家、诗人赵孟頫的绢本画轴里的杜甫像。
画中的杜甫獐目酒糟鼻,目光温和,面额圆润扁平,衣饰简朴,头戴斗笠,踽踽独行,展现了杜甫在颠沛流离的生活折磨下的真实形像。画上有明代主持纂修永乐大典的大学士解缙和元未明初文学家、吏部尚书刘崧的题跋。

在西川和东川合并后,统归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、充剑南节并使严武管辖,(类似现主管党政军的省委书记)权倾巴蜀。见《旧书·地理志》:剑南东川节度使,治梓州,管梓、绵、普、陵、遂、合、泸、渝等州。又考《会要》,上元二年二月,分为两川。广德二年正月,复合为一道。
杜甫与“同案犯”,掌管梓州军权的梓州刺史章彝交情深厚,当时作为严武属下的“厅级干部、军分区司令”章彝在梓州大搞军事演习,杜甫作诗吹捧之:
君不见东川节度兵马雄,校猎亦似观成功。
夜发猛士三千人,清晨合围步骤同。
禽兽已毙十七八,杀声落日回苍穹。
幕前生致九青兕,骆驼礨峞垂玄熊。
东西南北百里间,仿佛蹴踏寒山空。
有鸟名鸲鹆,力不能高飞逐走蓬。
肉味不足登鼎俎,何为见羁虞罗中。
春蒐冬狩侯得同,使君五马一马骢。
况今摄行大将权,号令颇有前贤风。
飘然时危一老翁,十年厌见旌旗红。
喜君士卒甚整肃,为我回辔擒西戎。
草中狐兔尽何益,天子不在咸阳宫。
朝廷虽无幽王祸,得不哀痛尘再蒙。
籍贯江苏的章彝原是严武幕下判官,由严武提拨为梓州刺史,本属幕僚,但不知那里与严武结下了“梁子”,也许严武疑手握重兵的章彝有谋反之嫌,于是在广德二年将章彝罢免,章准备赴朝廷复命时,被严武招回成都杖杀。杜甫作诗云:
《奉寄章十侍御》
淮海维扬一俊人,金章紫绶照青春。
指麾能事回天地,训练强兵动鬼神。
湘西不得归关羽,河内犹宜借寇恂。
朝觐从容问幽仄,勿云江汉有垂纶。
见《旧唐书·严武传》:武再镇蜀,恣行猛政,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,及是小不副意,赴成都,杖杀之。【鹤注】考二史,皆云严武杀梓州刺史章彝,此诗云“朝觐从容问幽仄”,意必彝将入朝,而武杖杀之也。
性格怪诞的杜甫没把握政治角度,没占好队,加之诗人放纵不羁的性格和正义,屡次激怒上级,终于把“严书记”给惹毛了,差点遭来杀身之祸,不是严母念及家庭世交出面劝阻,可能也跟章彝一样,召回成都杖杀了。很庆幸杜甫没有在当时死去,如果没有接下来的时日,我们就不可能接触到杜甫的诗句,杜甫的才华和名气就真的被埋没了。

按说,杜甫当时流落成都和三台之间,官职低微,生计困难,而严武又是封疆大吏,很需要严武的关照和靠山。如果他对严武的劣迹佯装不睬,缄口沉默,一如既往地友好下去、赞美有加,杜甫完全可以保全自己,躲在严武的卵羽之下过安逸的日子。但是杜甫没有这样做。他没有因为是世交而袒护他的恶行,他没有为了依附严武的权威而卖身投靠,他没有因为惧怕严武的暴戾而保持沉默。他不顾一切地对严武发飙,完全是出于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和正义感,是奋不顾身地对恣官暴吏的严厉斥责和批判,所以杜甫一生,“错把陈醋当做墨,写尽半生都是酸。” 作者 | 吴功斌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