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上注册,三台事早知道!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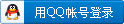 |
|
x

怀念我的父亲
作者:古往今来
蜂飞蝶舞,落英缤纷。都市人等,郊游踏青,尽情享受着无限春光。而我的心,却独钟于老家那一方绿色。
清明前夕,我和老伴儿回老家祭祖,勾起我一段难忘的家乡情怀。
天空澄澈,艳阳高挂,秀水漾漾,青山苍苍。我心心念念的家乡---四川省三台县古井镇李子园村古家堰那片开阔地上,麦田碧绿,桃园粉红。一位头戴草帽的农民,正操持着“突突”作响的旋耕机在桃林的间隔空间耙地,为播种大春作物做准备。
我碎步徐行于诗画般的田间的小路上。不远处,漫山遍野的柏树,郁郁葱葱,不见山路。耳畔,春莺恰恰,雄鸡喔喔。一个深呼吸,花香入肺,浑身有说不出的舒坦和惬意。行走间,我被地埂旁边嫩绿泛滥的桑树枝条拦住去路,脑子里忽然跳出《诗经》里“维桑与梓,必恭敬止。”的句子来。我知道桑梓分别是指桑树和梓树,桑梓是家乡的意思。由此看来,古人对自己家乡的感情是多么的毕恭毕敬啊!我的老家虽然没有梓树,但比比皆是的桑树可是有故事的桑树啊!
抚摸迎接我于路旁的桑枝良久,感慨万千,心有千言万语,却无从说起。我知道,人与植物是无法用语言沟通的。
握别桑枝续行,来到儿时年年戏水度夏的小河畔,驻足小石桥南侧的小码头,举目谛视,临近小河的地埂上,弧柳桃花,映入水中。“红入桃花嫩,青归柳叶新。”想必杜工部当年亦是春游临水,目睹如我所见的美景,诗泉的灵感涌入笔端,方有如此绝美的佳句流传后世吧。
目光聚焦河滩,那片20多亩茂密的杞木林叶子嫩嫩的,绿绿的,甚是醉人。让我这个看腻了高楼、听腻了喧嚣的城里人,倍感耳目一新、心旷神怡。
走过小桥,沿着熟识的山路,穿过密集的翠柏丛林,来到父母长眠的坟前,焚香点蜡,烧一摞纸钱,算是为人子的一点心意罢了。我是个唯物主义者,明明知道,人死如灯灭,可还是每年都这样,为的是记住父母的生育情、养育恩。如此而已。
看着坟茔周边林立的柏树---50年前才10几厘米高,它们现在业已枝繁叶茂,身高四五米,腰围都比碗口还粗了。睹树思人,梳理尘封半个世纪的记忆碎片,那个当年酷爱种树、管树的父亲形象,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。
1970年,我正读初中。一个星期天,父亲跟我一起出门,说是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便刨根问底想知道到底做什么事情。父亲说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临行前,我按照他的吩咐把床单叠好带上,跟着肩扛竹竿的他去了我家自留山。
来到一排大柏树下,父亲铺好床单,然后使劲儿拍打柏树果实。我以为,父亲这是要采集柏树种子,拿到街上去卖钱。我就呆呆地在那里,幻想着买肉改善伙食,清口水只往上冒。然后继续往好处想---买肉打牙祭之后,被母亲叫过去,一块新布披在我肩上,母亲伸开大拇指和中指,丈量着我肩膀的宽度,为我量身定做新衣服,心中顿生一番况味,心情一下子美出了新高度。
列位看官或有所不知,在那个缺衣少食的“大锅饭”年代,半年吃一次肉,一年到头给孩子们穿新衣,在农村是普遍现象。
龙门阵接到摆。父亲把柏树果子弄回家,我便天天盼着出太阳好晒柏树种子。果然,日随人愿,天气给力。一连几天,每天早上我都起得比往日早,把两根高板凳搬出去放在家门前的院坝里,然后把簸箕放在板凳上,将柏树果子摊开晾晒。五天后,柏树果实全部开裂了,把簸箕一阵颠簸抖动,柏树种子就出来了。剔除果壳和柏树的细叶,种子继续晒。就这样,早晾晚收,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
柏树种子晒干了,我便急切的问父亲好久拿去卖?父亲没有回答。过了一段时间,我发现父亲在家门前挥锄弄土筑埂子,围成一方苗圃,然后把我辛辛苦苦晾晒的哪些柏树种子拿去撒在地里,接着就是浇水。看到这样的场面,我热情洋溢的心一下子凉凉了。
“报复”的机会终于来了。那天,母亲叫我去喊父亲回家吃早饭,我的小情绪突然爆发,走了一圈回来,谎称已经完成任务。心想,哼!就要让你挨饿,哪个喊你不把柏树种子拿去卖钱,害得我心愿落空,白忙乎一场。
几乎每天一大早,父亲都会去他的苗圃地看看,蹲在埂子上,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。苗圃地每长出一根杂草,他都会把它拔掉。该施肥了,父亲就去自己家茅坑旁挑粪喂它们,期盼密密麻麻的小树苗快快生长。
需要说明一点,整个种子采集和育苗过程,父亲全都是尽义务,没有要队里一分一厘的工分。父亲说,他是党员,是队长,要带头讲奉献。
柏树苗疯长到20厘米高左右,父亲就号召全体社员移栽树苗。他说,无论是自留山,还是公山,都要栽柏树,树苗管够。
我们生产队,泥土厚一点的山,差不多都分给每家每户做自留山了。贫瘠的山坡,成为公山。自留山不必说,大家一呼百应,积极行动栽上了树苗。可要说绿化公山,社员大会上很多人都反对,说公山土脚太薄,不宜栽树,就是栽了,也不易成活,瞎子点灯---白费蜡。还有的说,即便活下来,也长不高,长不大。父亲说,必须栽满,是死是活,不用你们管。
面对不少反对派的意见,父亲作为一队之长力排众议,以权谋公。参加种树的记工分,拒绝参加的扣工分。别说,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,这一招还挺管用,几十亩浅草稀疏的公山荒坡,几天就披上了绿装。后来,父亲利用工余时间,在公山上义务补种了许多死去的树苗。
或许是树小林密,山间那几块地里的泥土被雨水冲下来,被荒坡上一众树苗和小草挽留下来,加厚了土脚,才让那些树苗的根往下扎,由浅而深,越串越远,树也由小而大。几十年的风风雨雨,才有了今日的满目苍翠、土树相依,不离不弃。
小河边那片10十几亩平坦的河滩地,就像“唐僧肉”一样,每年洪魔路过,都要“咬”上一口。当了一辈子农民,父亲见了心疼,于是又如法炮制,开始义务培育桤木树苗,把那片荒河滩全栽满了桤木树。小河沿岸3公里,还插上了柳树。桤木和柳,喜水易成活,并且特别肯长,五年成林,十年成材,成功地护住了那片荒河滩和岸边那一大片的耕地。
除了柏树、桤木和柳树,父亲对桑树也感兴趣。父亲50多岁退出队长职务以后,主动要求去生产队的地埂、田埂的斜坡上和河边沙地里栽种桑树。他说他喜欢树,现在老了,干不动重活,但每天会自觉地去努力工作。至于工分,我不计较,你们觉得给多少合适就给多少。反正我的工作就是种树、管树。
就这样,种树管树成为老爸的日常。他独自一人每天扛着挖锄,把埂子上的土挖松,除尽杂草,然后挖成一个个小坑。就这样,一个老人,早出晚归,寒来暑往,用满是厚茧的双手干了一年多,硬是把一万多个树窝挖好了。适宜栽桑的时间节点到了,父亲建议年轻队长安排人力,统一栽上了桑树。
三分种,七分管。十多年管树的过程,更是漫长而艰辛。一年四季,只要天不下雨,父亲都会去除草,松土。冬天寒风凛冽,他坚持要去剪修枝条,给桑树穿上“白裙子”(涂刷石灰水防虫害)。
三年后的冬天,父亲到公社请教技术员,学着嫁接桑树。回到队里,用了四个冬天,硬是把生产队一万多株细叶桑全部嫁接成叶阔肉厚的良桑。为后来推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,土地分包到户后群众养蚕致富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父亲一生对种树情有独钟,不光是绿化生产队的荒山荒滩和地埂,还号召每家每户房前屋后栽竹种树,应栽尽载。我清楚地记得,当年我家屋后栽竹子,房前栽黑桃、香椿、桉树,自留地埂子上则栽桃树、橘子。父亲用过的那把大约巴掌宽、一尺多长的挖锄,长年累月跟泥土摩擦,长度减少了一大半,锄身却磨得锃亮锃亮的。直到土地包产到户,那把短而亮的挖锄还被他用来继续干活。直到1993年父亲80岁去世前,他还在坚持为家门前哪些果树除草施肥,喷药治虫。
20多年后,家乡的80后、90后外出打工挣钱,泥巴墙支撑起的鳞鳞瓦房不见了踪影,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一楼一底、两楼一底的小洋楼。房屋结构变了,但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栽竹种树的习惯没有变,很多家庭还种的是果树。村里老人们都说,修楼房就是好啊,省去了木料,现在村里再也没人去砍树建房了。
纸钱早已化为灰烬,我仍然伫立父亲坟前不愿离去。我心里默默地念道:父亲啊,你一生淡泊名利、低调做人,虽然在枪林弹雨的朝鲜战场出生入死、屡建战功,最高功勋级别已达一等功臣,却从不居功自傲。你当队长那些年,没花国家一分钱,带领生产队的社员自力更生采石架桥,建起一座集拦水堰和人行石桥为一体的石河堰---古家堰,让队里群众不再冒着生命危险蹚水过河去古井街上赶场。再说了,把小河水拦起来,让电灌站有了可抽之水,才有了队里的一百多亩庄稼地旱涝保收,才有了林茂山青、房前屋后硕果满枝的“生态银行”
。儿子相信,你老人家留给家乡这一片片价值不菲的生态遗产,必将泽被子孙,福及后代。
黄土掩白骨,青山埋忠魂。父亲啊,你平凡劳碌一生,入土以后,儿子也没有给你们立块碑。我想,作为“树痴”的你,周围有这么多你喜爱的大柏树相伴,本身就是一块块比石碑更具生命力的丰碑!历史不会忘记,家乡人民不会忘记,青山绿水更不会忘记!愿父亲在翠柏间安息······
|